一、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出生于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司马迁6岁,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说,司马谈一直想效法孔子写作《春秋》的精神,写一部体系完整的史书,可惜他只做了一些准备的工作,便病逝于洛阳,临死之前,把他的理想事业,交给了儿子。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期担任太史公,担任史官,同时为完成父亲愿望,创作了《史记》。
司马氏是世官担任太史,司马迁的历史创作一直到太初末,共有130篇,到他去世后终止。史学界认同司马谈参与了创作少数篇幅,但是从内容和笔法、体例的贡献看,该书基本都是司马迁创作,虽然缺失了万字,但大体保留了原貌。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踏遍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各地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对以后编写《史记》有很大帮助。
《史记》还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
二、班固和他的《汉书》。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大臣、史学家、文学家,与司马迁并称“班马”。
班固是班彪之子,班超之兄,十六岁入洛阳太学,二十三岁父死后归乡里。以父所撰《史记后传》叙事未详,乃潜心继续撰述力求精善。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被人诬告私改作国史,下狱。其弟班超辩明其冤,出狱后被任为兰台令史,奉命撰述东汉开国以来史事,与陈宗、尹敏、孟异等共撰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又自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明帝复命他完成前所著书。他认为《史记》以汉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不妥,决心撰写起自汉高祖、终于王莽共二百三十年事迹的《汉书》。汉章帝时,以文才深得器重,迁官玄武司马。建初四年(79年),章帝召集诸儒在白虎观讲论五经同异,命其记述其事,撰成《白虎通德论》(一名《白虎通义》)。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随窦宪出击匈奴,为中护军,参预谋议。次年,行中郎将事。永元四年,窦宪失势自杀,他受牵连免官、被捕,死于狱中。
班固一生著述颇丰。作为史学家,修撰《汉书》,是“前四史”之一;作为辞赋家,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两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列入《文选》第一篇;作为经学理论家,所编《白虎通义》集当时经学之大成,将谶纬神学理论化、法典化。
由《史记》到《汉书》,对项羽的记载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产生的原因有很多,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历史理念不同。司马迁对儒家并不是完全推崇的,正如他在《史记》中所说的那样:“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这就导致了他能够相对客观地说明了楚汉战争中的史实,当然这并不代表司马迁毫无立场可言。而班固持有较强的正统观念,因而他在作《汉书》中对一些史实进行了取舍,凸显了汉王朝的正统地位。
第二,评价标准不同。班固等后世史家在认识项羽时,往往会在潜意识里把他与刘邦相对比;相应地以一个君主的标准来评价他。而通过《史记》的记载,我们发现项羽虽不是一个合格的君主,却是一个良好的武将。因为他在君主的位置上,所以他身上不适合做君主的性格特征大都被放大,成为了他的缺点。再加上“成王败寇”思维的影响,使得后世史家对项羽的评价大都存在一定的偏差。
三、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省夏县)人,出生于光州光山(今河南信阳光山县)。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代。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及第,累迁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名列“元祐党人”,配享宋哲宗庙廷,图形昭勋阁;从祀于孔庙,称“先儒司马子”;从祀历代帝王庙。
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需要说明的是,在以上三部正史中,只记载了项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到他三十一岁自刎乌江时的八年史事。这些历史,部分读者已有所了解,在本书中不再详细论述。在八年的正史记载中,近五年楚汉之争的故事广为人知,在本书中我写得简略一些。由于项羽的主要功绩在于三年的亡秦战争,这并不是广大读者所熟知的,我就介绍得详细一些。项羽是杰出的军事家,在本书中,更多的是从军事角度记叙这八年的历史。在本书中,我尽可能详尽的探究项羽二十四岁以前的心路历程,尽可能客观公正的介绍项羽两千年来的巨大影响。
四、秦汉时期的历法
颛顼历,秦朝历法,是中国古六历之一。相传“颛顼历”在周朝末期已经制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颁行全国,以十月一日为元朔。颛顼历自秦始皇二十六年至汉武帝太初元年共行117年。
据说该历采用的是十九年七闰法,一回归年为365又1/4日(所以是一种四分历),一朔望月为29又499/940日,以十月为岁首,闰月放在九月之后,称后九月。测制年代或为秦献公时公元前366年,至秦始皇一统天下后遍行,经秦朝至西汉太初历制定(公元前104年)始弃。今人朱桂昌著有《颛顼日历表》,是本书编写的依据。
五、年表:
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然而真正有文献记载年代的”信史”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此前的历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过,他看过有关黄帝以来的许多文献,虽然其中也有年代记载,但这些年代比较模糊且又不一致,所以他便弃而不用,在《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无具体在位年代。因此共和元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年表。
第一个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学作系统研究工作的学者是西汉晚期的刘歆。刘歆的推算和研究结果体现在他撰写的《世经》中,《世经》的主要内容后被收录于《汉书·律历志》。从刘歆以后一直到清代中叶,又有许多学者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进行了推算和研究。这些工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他们推算所用的文献基本上不超过司马迁所见到的文献,所以很难有所突破。晚清以后情况有些变化,学者开始根据青铜器的铭文作年代学研究,这就扩大了资料的来源。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又为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来源。进入20世纪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又为研究夏商周年代学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版权说明:
《白话史记》(全译本)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台静农先生的倡议下,汇集了台湾十四所院校六十位学人,经过两年的努力,将《史记》全部语译,凡一百六十万字。由台静农先生题写书名并作序出版。司马迁的《史记》贯穿经传,整理诸子百家,纂述了三代而下以至其当代的史事,为中华民族保存了纪元前千余年的历史文化,这一巨著,是先秦所有典籍无可相比的。作为一个中国人,要了解自已的历史文化,必读《史记》。唯有透过《史记》的认识,才能真正找出中国人的“根”。但因其文字古质,没有相当学力的人是不易读懂的。尤以今时学术分科,除专门文史学研究者外,有能力读此书的更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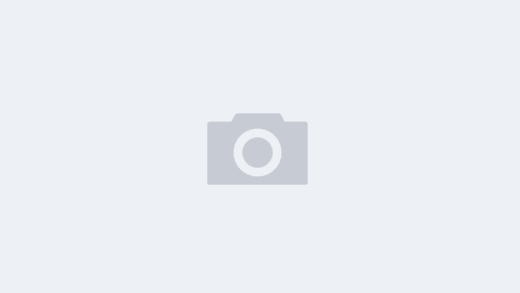
 苏公网安备32131102000660号
苏公网安备32131102000660号
年表后增“天文”。
荧惑守心,五星聚东井,几次日食等。
荀悦(148-209年),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东汉史学家、政论家,思想家。名士荀淑之孙,司空荀爽之侄,其父荀俭早卒。
汉灵帝时期宦官专权,荀悦隐居不出。献帝时,应曹操之召,任黄门侍郎,累迁至秘书监、侍中。侍讲于献帝左右,日夕谈论,深为献帝嘉许。后奉汉献帝命以《左传》体裁为班固《汉书》作《汉纪》,写成《汉纪》30篇。建安十四年(209年)逝世,年六十二。
荀悦另著有《申鉴》5篇,抨击谶纬符瑞,反对土地兼并,主张为政者要兴农桑以养其性,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表现了他的社会政治思想。还著有《崇德》。
《汉纪》是记述西汉历史的史书,体例为编年体,三十卷,作者是东汉时期的荀悦。荀悦(公元148年~公元209年),字仲豫,汉献帝时做过侍讲,后来任秘书监、侍中。著作有《申鉴》等。汉献帝觉得班固的《汉书》难懂,于是让荀悦根据《左传》编年纪事的体例重抄《汉纪》供他参阅。
《汉纪》共约十八万字,不足《汉书》的四分之一。时间起于二世元年(前209年),止于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虽然《汉纪》的内容几乎全部来自于《汉书》,个人创作较少,但它促进了古代史书编年体的成熟与完善。另外荀悦虽然是”抄书”,但被梁启超称为” 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
《汉书》将项羽记入列传(陈胜项籍列传第一)事,应详写,以向普通读者介绍。
《楚汉春秋》,九卷,西汉陆贾撰。所记从刘邦、项羽起事起,至汉文帝初期止,为一部杂史。司马迁撰《史记》时,曾采撷此书。西汉末年后散佚。清人有三种辑本,一、洪颐煊所辑,见《问经堂丛书》。二、茆泮林所辑,见《十种古逸书》,亦见《后知不足斋丛书》和《龙溪精舍丛书》。三、黄爽辑本,见《黄氏逸书考》。其中以茆辑最佳。但佚文数量不多,史料价值亦有限。《楚汉春秋》完整版本至南宋时开始失传,清朝的茆泮林、洪颐煊和黄奭对楚汉春秋进行过辑佚工作,内容分别保存在《龙溪精舍》《问经堂丛书》和《黄氏逸书考》中。
创作背景
与《新语》的写作目的相似,《楚汉春秋》意欲通过记录时功,反思历史,总结历史教训,为汉王朝提供借鉴。主要内容为秦末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的历史,所记之事自刘邦、项羽起事起,至汉文帝初年止。书法不隐,直书其事,亦足以成一家之言,开创汉代私人撰写当代史的先例,文献价值较高,是了解楚汉争霸的最直接、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史记》叙述此段历史便以此为据,“刘氏初兴,书唯陆贾而已。子长述楚、汉之事,专据此书”(刘知几《史通通释》)。除了《史记》所引之外,尚有一些《史记》所未及者,如“高祖向咸阳”“美人和项羽歌”“淮阴武王反”等。部分篇章文字优美,形象鲜明。
《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皆言此书9篇,至宋代已散佚。清代辑佚的本子有洪颐煊的《问经堂丛书》本、茆泮林的《十种古逸书》本、黄奭的《黄氏逸书考》(《汉学堂丛书》)本,其中以茆本为佳,《后知不足斋丛书》《龙溪精舍丛书》均收录此本。今人点校本有齐鲁书社于2000年吴庆峰校点的《二十五别史》本。
书籍内容
《楚汉春秋》记载的是秦末刘项争夺天下的历史。陆贾以当代人写当代事,一定真实可信。所以《汉书·司马迁传》云:“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四库全书总目》的《新语》提要云:“迁取《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作《史记》。”可见此书的重要性。
作者简介
《楚汉春秋》是西汉时期的陆贾所撰。
陆贾,楚人,跟随刘邦打天下,以能言善辩出使诸侯。汉朝建立以后,他提出以儒家思想治理天下,写成《新语》,为新王朝的发展提供思想指导。他还出使南越,说服南越王赵佗称臣,又协同陈平、周勃诛除诸吕,为汉朝的局势稳定作出重大贡献。
《通鉴纪事本末》是南宋袁枢编辑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也是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凡四十二卷。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共1300多年。文字全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文,只是撰写方式改易。取《资治通鉴》所记之事,区别门目,分类编排。专以记事为主,每一事详书始末,并自为标题,共记239事,另附录66事。开“纪事本末体”之先河。为了方便阅读,分为战国至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四部分。
《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枢(1131—1205年),字机仲,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中进士,历任温州判官、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学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职。他晚年喜易,著有《易学索引》、《周易辩异》等书。
袁枢为人正直,对政治腐败,朋党互争,压制人才等丑恶社会现象是很不满的。当他为国史院编修官,分配负责撰修《宋史》列传时,北宋哲宗时“奸相”章惇的子孙,以同乡关系请袁枢对章惇传加以“文饰”时,袁勃然大怒说:“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天下公议!”(《宋史·袁枢传》)宰相赵雄“总史事”听到后,即称赞他“无愧古良史”(同上)。
当时现实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给内外交困的赵宋封建政权提供安邦治国的药方。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解决读《资治通鉴》的困难。由于《通鉴》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实,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记述,对于一件事情连续好几年的,它未能连贯记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阅好几卷,读者很不方便。
据说,《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希望写作班子以外的有关人员再看一遍,但使他很失望,只有一个名叫王胜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别的人面对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几卷,有的只看了几页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见,《通鉴》由于篇幅太大使人阅读困难。司马光本人也感觉到这一难处,他晚年时曾经想另写一部《资治通鉴举要历》,把《资治通鉴》简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从心,结果没有完成。
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虽然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编写《通鉴纪事本末》,但他熟读《通鉴》却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时间。他不但要熟读《通鉴》,了解其全部内容,还要吃透司马光的史学见解。袁枢跟司马光一样,始终恪守“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原则。因此他在编立标题,抄录史料时,对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鬼怪等绝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这种反对天命论神学,而重视社会现实的史观,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对于统治者袁枢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枢在《通鉴纪事本末》卷三《武帝惑神怪》中抄录了“臣光曰”,批评了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由此可见,袁枢是有自己的政治见解的,这正如朱熹所说的,袁枢“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朱子大全》卷81)所谓“微意”,就是指袁枢的政治观点。袁枢把有关封建政治的主要问题,如杨万里(与袁枢同为太学官)所举的内容,“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通鉴纪事本末叙》)之类,都作为全书的基本内容,使它成为当时及后世君臣的鉴戒。袁枢还十分重视汉族政权的恢复事业,对于“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书特书,而对于进据中原及举兵南犯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分子,则视为“石勒寇河朔”,“赵魏乱中原”。当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到《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时,立即推荐给宋孝宗。宋孝宗阅读时,赞叹地说:“治道尽在是矣。”(《宋史·袁枢传》)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赐太子和江上诸帅,命熟读之;还提升袁枢为大宗正簿。袁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从而出现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体例。以“时”为中心的编年体和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各有千秋,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的共同缺点。而袁枢创立的以“事”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裁,却弥补了编年与纪传体的不足,因而丰富了史学内容,正如清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所评论的那样:“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文史通义·书教下》)章氏的评论是正确的,袁氏创立的纪事本末新体裁,的确是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一大贡献。虽然《通鉴纪事本末》原抄《资治通鉴》,但对《通鉴》的校勘却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通鉴》流传已久,传抄刻印,难免会有错误。所以我们读书时,可以把两书互相校勘。清代的张敦仁曾经用《通鉴纪事本末》大字本(即湖州版本;严州版本字小,又叫小字本),和明代万历年间杭州所刻《资治通鉴》元注本互校,校出异文3000多条,写成《资治通鉴刊本识误》3卷,后来章钰撰写《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时,把张敦仁校勘《资治通鉴》的异文而无别本资印证处,列为附录。1957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标点本《资治通鉴》,除了章钰书中重要校勘都收入本书做注文外,还选录了张敦仁书中的一些校勘做为注文。这就使标点本《资治通鉴》成为现有较好的一种版本。
《通鉴纪事本末》的价值,首先是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提供了一部为统治者所急需的简洁明畅的历史教科书。我们都知道,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为“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而编写的,但由于其体例方面的原因,要想通过阅读《资治通鉴》来了解历史经过,明了其中“废兴存亡”的道理,汲取经验教训,存在很大困难,这就需要一部简明而又总结治乱兴衰道理的历史著作。袁枢用纪事本末体重新构建编年体的《资治通鉴》,正是满足现实迫切需要之作。书成后,宋孝宗极为看重,就作为教科书马上分赐给皇太子和带兵守边的统帅,这说明了这书的确有很大的资治作用。
《通鉴纪事本末》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就是在今天看来,它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化简了《资治通鉴》,便于阅读和传播,可以作为我们学习历史的入门之书。《通鉴纪事本末》中所选事件,都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并且每事都分立标题,概括出其中心内容,然后详述其始末,线索单一、中心明确、掌握快捷。加之袁枢所选事件,基本概括了每段历史的面貌,读《本末》,很快就能知晓历史大概。所以,它是我们学习历史的一部入门之书。
《通鉴纪事本末》还整理了史料,便于检索校勘,也是一部工具之书。《资治通鉴》按年编排史料,相关的史实,处在不同的时段里,便被分割开来,这样,就造成了相关史料处于分散和零碎状态。《通鉴纪事本末》把与一件事相关的所有史料集中在一起, 为我们检索查找提供了方便。举例说明,如历史上的西晋时期,从建国起,就变乱不断,每一次变乱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怎样,在《通鉴》中,这些史料就被分散于整个西晋的五十多年中,要想了解这些情况,从《通鉴》中去寻找,就相当不易,而通过《本末》去查找,那就极为方便,它以“西晋之乱”立一标题,又列出副题;“贾氏、诸王、胡羯、江左中兴附”补充说明。然后从《通鉴》中辑出西晋一代有关变乱的所有资料,始于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年),晋王娶王肃之女,止于东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年)春。集中在一个篇章中叙述,极便于检索查找。
《通鉴纪事本末》一书,不仅因其以上的史学价值为人既目,更重要的是以其创立的纪事本末体,在中国史学史上树起了不朽的丰碑,这种以事为纲的纪事本末体,是对中国封建史学上千年发展的总结,并已在其中蕴含了新时代史学的胚胎。它在编年体和纪传体之外,创立了新的编撰方法,推动了封建史学的发展。在《通鉴纪事本末》的启发和影响下,出现了许多用纪事本末体编撰的历史著作,《四库全书》中收入史部的纪事本末类著作有二十二部,存目四部。至本世纪三十年代,王云五主编《续四库全书》,收入史部纪事本末类的著作有一百零九部,不包括《四库全书》已收录的著作。它们在基本遵循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创作方法之外,还有所改进,特别是在史料的排比整理和增补修订等方面,做了不少新的尝试。
缺点
《通鉴纪事本末》也有它的缺点。首先表现在取材上,因《资治通鉴》本来就是一部政治史,关于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载比较少。袁枢所取资料,不过是有关诸侯、“大盗”、女主、外戚、宦官、权臣、“夷狄”、藩镇之类,其他史事,多略而不书。这不能不是一个欠缺。另外,它囿于《资治通鉴》范围,多属照抄,没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
总之,《通鉴》有的,它不一定都有,《通鉴》没有的,它也没有。其次,《通鉴纪事本末》记述的事与事之间没有联系,对于整个历史不能勾画出一个发展的线索,因此,它只能记述了“治乱兴衰”的现象。还有,《通鉴纪事本末》具有明显的敌视农民起义的思想。例如,对于农民起义,多称为某某之乱(如“黄巾之乱”)。
版本
《资治通鉴》是一部浓缩了中国古代政治运作、权力游戏的历史巨著,但它采用编年体,事件分散,阅读起来头绪纷乱,难得完貌;南宋袁枢用完整记录事件本末的方式整编《资治通鉴》,编著了《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将1300多年的历史,转换为一个个完整连续的故事,给阅读带来极大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