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九连就打了这一仗。
当我抱着手榴弹闯进敌洞时,洞内漆黑啥也看不见。我贴着洞壁朝前摸,摸进十几米,才听见里面有动静。敌人显然也听到我进来了,射来一串子弹,却没有打中我。我便将一捆手榴弹拉了弦,扔了过去。之后,我就啥也不知道了。
后来,是代理副连长带领大家,象掏老鼠洞一样又掏了两个敌洞,又炸死了十三个敌人,战斗便胜利结束了。
我是被自己甩出去的那捆手榴弹炸晕的,伤得并不重。这时,我们营的七连奉命赶到364高地,接替了我们九连。
我先是被送到师战地医院,接着又转到国内。十几天后,我的伤就痊愈了。
整个部队班师回国,凯旋门前是人海鲜花,颂歌盈耳;庆功宴上是玉液琼浆,醇香扑鼻。当活下来的我重新体味生活的美好和芳香时,—想起连里殉国的英烈们,我的心情分外沉重。
部队展开了评功活动。军里决定报请军区,授于我们九连为“能攻善守穿插连”的荣誉称号。经过群众评议,我们九连党支部决定报请上级党委,分别授于梁三喜、靳开来、还有不知姓名的战土“北京”为战斗英雄称号……
对梁三喜和“北京”同志,团里没有争议。对靳开来,不管我们党支部怎样坚持,却连个三等功也不批!这时,有人竟提议授予我英雄称号,说我在战斗最困难的时刻,第一个只身闯进敌洞炸死九个敌人,称得上什么“模范指导员”!
我被刺眼的镁光灯和接踵来访的记者包围了。
记者们对我好象尤其感兴趣,连我的名字也具有特别的诱惑力。有位记者说我当年出生在沂蒙战场上,现在又在战场上立了功,很值得宣传。他以抢新闻的架势找到我,对我进行单独采访。并说他已想好了一篇通讯的题目:正题是《将门生虎子》,副题——记革命家庭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英雄赵蒙生。他让我围绕着这个题目提供材料。我当即把我参战前后的情况如实给他说了一遍,一下打乱了他的构思。但他仍坚持要宣扬我,并说了一大套理由:什么报道要有针对性啦,用材料要去芜取精啦,因此不需面面俱到,要以正面表扬为主……
我坚决拒绝了他:“要写,就真真实实地写,别做‘客里空’式的文章!”
是的,战争刚刚打罢,烈士尸骨末寒,我怎敢用烈士的鲜血来粉饰打扮自己!
评功活动完结后,接着进行烈士善后工作。我们连在全团是伤亡最大的连队。团里派出专门的工作组,来帮助我们做这项工作。
烈土善后工作进行极为顺利。烈士的亲属们深知亲人是为国捐躯,个个深明大义,没有谁向我们提出过任何超出规定的要求。他们最关心的是亲人怎样牺牲的。我向他们一一讲述烈士的功绩,并把授结烈土的军功章捧献给他们……
但是,当我面对靳开来的妻子和那四岁的小男孩时,我为难了。我向烈士的遗妻和幼子,讲述了副连长怎样带尖刀排为全连开路,怎样炸毁了两个敌碉堡,又怎样坚守无名高地消灭敌人。当然,我省去了副连长带人去搞甘蔗曲事,我只说副连长在阵地前找水踩响了地雷……
当靳开来的遗妻抬起泪眼望着我,对这位来自河南禹县一个公社社办棉油厂的合同工,我已无言安慰。所有烈士亲人都有一枚授于烈土的军功章(大部分是三等功)。唯独她没有……
我拭泪把我的一等功军功章双手捧给她:“收下吧,这是我们九连授给一等功臣靳开来烈土的勋章!”
这位憨厚纯朴的女合同工,双手按过军功章捧在胸前凝望着。过了会,她才把这军功章连同靳开来烈土留下的那张全家幅一起包进手帕,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
她带着那四岁的小男孩,不声不响地离开了连队。
谢天谢地,她并不晓得连队是无权决定给谁立功的(哪怕是记三等功)!我默默祝愿,祝愿那枚军功章能使她在巨恸中获得一丝慰藉,也企望那四岁的孩童在晓明世事之后,能为父辈留给他的军功章而感到自豪!
烈士亲属们都一一返回了。唯独不见梁三喜和“北京”同志的亲属来队。团政治处已给山东省民政部门发了电报和函件,请他们尽快通知梁三喜烈士的亲属来队。战士“北京”的真实姓名,在部队回国后我们通过查找对号,得知他叫薛凯华。参战前一天从兄弟军区火速赶来的那批战斗骨干,团军务股存有一份花名册。当时把他们急匆匆分到各连后,几乎所有的连队都没有来得及登记他们的姓名。因此,全团有好几个连队都出现了烈土牺牲时不知其姓名的事情……
团、师、军三级党委,决定重点宣传粱三喜的英雄事迹。让我们连多方搜集粱三喜烈土的遗物、照片、豪言壮语以及有宣传价值的家信等等,以便送到军区举办的英雄事迹展览会上展出。
当我着手组织搞这项工作时,确实作难了。
梁三喜的遗物,除了一件一次没穿过的军大衣外,就是两套破旧的军装。团里派人把两套旧军装取走了,因那打着补丁的军装,足能说明烈士生前身先士卒,带领全连摸爬滚打练硬功。团里听说粱三喜有支“八撮毛”的牙刷,又派人来连寻找,因那“八撮毛”的牙刷,足能说明烈士生前崇尚俭朴。然而,很可惜,在那拚死拚活的穿插途中,梁三喜已把牙刷、牙缸全扔在异国的土地上了……
至于照片,我们到处搜集,也没能找到梁三喜生前的留影。最后,我们从师干部科那里,从干部履历表中,才找到一张梁三喜的二吋免冠照。这为画家给烈士画像,提供了唯一的依据……
我是多么悔恨自己啊!我曾身为摄影干事,下连后还带着一架我私人所有的“YASHIKA”照像机,却未能为梁三喜摄下一张照片!
至于梁三喜写下的豪言壮语和信件,我们也一无所获。梁三喜是高中二年级肄业入伍的,按说他应该写下很闪光的文字。但是,我们只找到一本他平时训练用的备课笔记本,全是些军事术语,毫不能展现烈士的思想境界……
参战前后,他在戎马倥偬中为我们留下的,就是那张血染的欠帐单!
这天,我把欠帐单拿到团政治处,想让团领导们看一下。然而,无独有偶。团政治处的同志告诉我。这样的欠帐单并不罕见。在全团牺牲的排、连干部中,有不少烈士欠着帐。五连牺牲了四个干部,竟有三个欠帐的。这些欠帐的烈土,全是清一色从农村入伍的。他们欠帐的数额不等,其中,梁三喜欠的帐数额最多。
看来,我对从农村入伍的排、连干部、以及那些土里土气的士兵们的喜怒哀乐,还是多么不知内情啊!
时间又过去了几天,仍不见粱三喜烈士的母亲及妻子来队。我多次催团政治处打听联系。这天,政治处来电话告诉我,他们已数次给山东省民政部门去过长途电话,查问的结果是:粱三喜烈士的母亲梁大娘、妻子韩玉秀,她们抱着个刚出生三个多月的女孩,起程离家己十多天了。
呵,十多天了?乘汽车、坐火车,再乘汽车……我掰着指头算行程,她们祖孙三代早该赶到连队来了呀!莫不是路上出了啥事?那可就……
我后悔自己工作不细,恨当初为啥不建议团政治处,让连里派人赶往山东沂蒙山,去接她们祖孙三代来连队……
我们连驻地不远有公共汽车停车点,我派人到停车点按了几次没接到,我更是忧心忡忡,日夜不安……
这天中午,师里的丰田牌轿车开进连里。我一看,是妈妈来了!
我忙把妈妈迎进宿舍里,给她倒了杯水:“妈……今天刚赶来?”我不知说啥是好。
“咳!坐飞机,乘火车,师里派车在车站接到我,我到师里坐了一会,就来了。”
我与妈妈相对而视,沉默无语。
妈妈比我临下九连回家休假见她时,明显消瘦了。她脸上失去了往常那乐悠悠的神采,眼圈周围有些发乌。
“你……怎么不给妈写信?”
“回国后事情太多。”
“你……你知道妈这些日子是怎样熬过来的呀!”妈妈眼泪汪汪,“妈是从报纸上……看到你们九连……妈才知道你没……”
我无言对答。
“那天晚上,妈要了三个多小时的电话,才……才好不容易要到‘雷神爷’。谁知,竟挨了他一顿……臭骂,打那,妈就夜夜做恶梦,一会梦见‘雷神爷’用手枪指着你,让你去……去炸碉堡,一会又梦见你满脸是血,呼唤着妈妈……”妈妈抹着泪,“妈知道在那种时候打电话也不应该,可‘雷神爷’他……他也太不讲情面了!妈是快往六十岁上数的人了,生来也不是怕死鬼!可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呀,要死,妈宁愿替你去死!”妈妈伤心地抽泣起来。
我该说啥呀?我没有资格责怪亲爱的妈妈!
妈妈的老家在皖北。早年间外祖父一家一贫如洗,妈妈八岁上就卖给了地主当丫头。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政府为躲过日寇南逃,炸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了豫东、皖北骇人听闻的黄泛。咆哮的洪水使外祖父一家全部丧生。妈妈当时十六岁,她是抱着地主家一只洗衣的木盆,才大难未死!当年秋,她只身流浪到沂蒙山投身革命,后来当过团卫生队的卫生员、护土长、“地下医院”的指导员,师卫生科长……再后来她随大军打济南,战淮海,长驱南下……妈妈参加过上百次战斗,满满一手帕勋章闪耀着她光挥的历程。她那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能写一部比砖头还厚的书啊!……
而我,只不过刚刚参加了一次战斗!
我感到心中燥热难挨,便摘下了军帽。
“天!这……这是怎的?”妈妈发现了我额角上的伤疤,“是……是枪伤?”
“不是。是被手榴弹片儿划了一下。”
“天呀!一点点……只差那么一点点就……”妈妈的声音在打抖,“疼,还疼吗?”
我摇了摇头。
望着不时拭泪的妈妈,我心中象打翻了个五味瓶。妈妈是那样宠我,疼我,爱我,到眼下还把我当成小伢儿一般!我也曾为有这样的妈妈,感到无比自豪、幸福、温暖!可眼下,妈妈的一举一动,竟使我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就连戴在妈妈手腕上那块“欧米格”坤表,和那熠熠生辉的表链,过去我觉得那样受看,眼下却觉得有些刺眼了。
“蒙生呀,咱不穿军装往回调啦,省得央这个,求那个!”妈妈擦干泪说,“血,你也为祖国流了,问心,咱也无愧了!边境线上看来还安稳不了,干脆就脱了军装转业吧!”
我摇了摇头。
妈妈吃惊地望着我:“怎么?你……”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妈妈。
此时,我只是觉得:母爱是神圣的,也是自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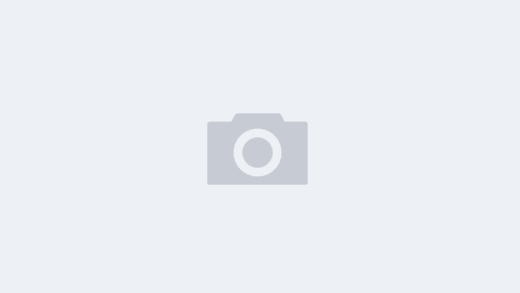
 苏公网安备32131102000660号
苏公网安备3213110200066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