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讲授国史,几次讲到我少年时代的国家工业状况,不谈数据,只说生活经验,因为我关于国家发展的许多观点都是从个人生活经验中提炼出来的。
还是1961年或者1962年,我已经在姑母家生活。一天放学回家,门口的人不算多,但在开会。一位干部讲话,要求今后大家对许多生活用品的叫法需要改口,比如,洋油要叫煤油,洋火要叫火柴,洋钉要叫铁钉,洋布也改叫布的本名,比如府绸布就是府绸布、咔叽布就是咔叽布,等等,连我根本就没见过的水泥也不叫洋灰了。我没有兴奋感,因为当时还不懂改变这些名称的意义。但是此前凡是生活中的工业用品,的的确确都在前面冠上一个“洋”字,那可是铭心刻骨的记忆。
上天是慈悲的,想让人们早早休息,总是请太阳到时下班。但是人们为了生计,却不得不继续忙碌,于是就有照明的需要。已在城里彻夜通明的电灯,对于乡下的人们来说,只是传说与想象中的照明工具,蜡烛也只有年节或者祭奠亡者才用,平时老辈常用菜油点灯。5、60年代,农村的人家已经多用煤油灯了,我晚上的作业就在煤油灯下完成的,鼻孔里的黑灰是偷看小说的印记。家里所有的生活琐事也都是在它的照耀下完成的,只有煤油不够才用菜油凑合一下。这种窘况直到70年代初期才真正结束,但已经不是我的家庭生活记忆,而是对社会历史的印象。
山顶洞人已经学会用火,但没有发明火。火的发明却是人类一切发明中最伟大的发明。燧人氏因为钻木取火,不仅被摆在三皇五帝之列,而且位列三皇之首,号曰羲皇。但只有洋火才是工业产品,才真正把人类引入近代文明。我从记事开始家里就用洋火,但是老辈们讨古时,还是时常提起过去用火石打火的情形。现在虽然有了洋火,人们的用度却十分节俭,祖父抽烟通常舍不得用火柴划燃,而是用黄草纸当媒子,引灶里的草料火点着自己烟锅里的烟丝。还有特别的情形,邻家断火,做饭了,就用一把绕紧的草料来到我家,点着后再举着火把回家做自家的饭。60年代初期,不仅火柴取代了洋火,而且越来越普通,甚至还有了打火机,但很精贵。
铁的发现和铁器使用,促进人类走进封建时代,至少有的历史学家是这么说的。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铁器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并没有得到充分使用。因为我的伯父一家在南京,我家与城市联系在村子里算是最密切的,所以洋钉在我家里不算稀罕物。但是祖父的工具箱里也就是那么几颗,不仅满身铁锈,而且大多卑躬屈膝低头哈腰。要在墙上挂个什么物件,父亲还是得把削尖的木桩楔进土墙的逢里。如果偶尔找到一根钉子,往往还没钉进墙里,已经折节屈尊。现在想起父亲当时的一脸惆怅,猜想他一定想找到一根更硬一点的钉子。如果不是这个时代之窘,估计人们也不会到处冒烟大炼钢铁,雷锋叔叔也不会捡起地上的螺丝钉,捡起来了也不会有什么模范意义。但是自从洋钉被叫作铁钉之后,铁钉也就逐渐走进千家万户,而且越来尖锐,越来越坚强,以至我们的筋骨里也有了更多的钢铁元素。
这样的生活实例不胜枚举,就是我们的曾经,就是我们的历史,也是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也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真实地刻录着国家一清二白的历史真相,同时也证明国家是怎样从一丝一缕、一点一滴开始,慢慢地积累起工业化的家当。不管时代怎么进步、飞跃,想起过去,就在心里浮现先人们踩着布满荆棘的荒原古道,泼洒着血泪与汗水,筚路蓝缕,开辟着通向今天的辉煌。那一个个佝偻的负重身躯就像成群的三峡纤夫,发出的喘息就像沉重而豪迈的川江号子,不仅是对现实的叹息,更是对未来的呼唤。
(2019年10月14日在芜湖)
作者:管中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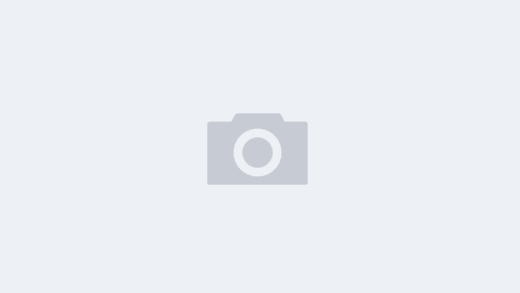
 苏公网安备32131102000660号
苏公网安备32131102000660号
敬请作者告知联系方式以支付稿酬。